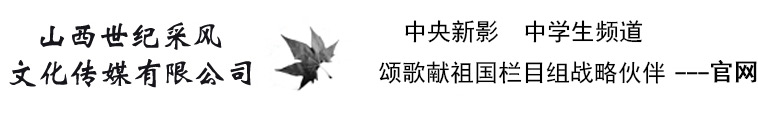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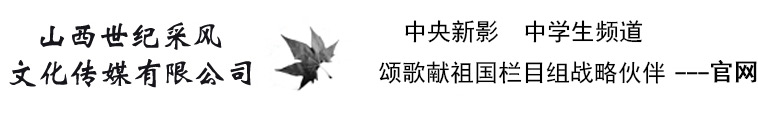
![]() 世紀采風
世紀采風
筆者按:這篇文章的初稿寫于2020年4月,是年6月又在《對野生高粱“易地生根”現象的探索》的文章里作為一個小標題“胚軸延伸體的發現與提出”。本來是按論文寫的,現在我把它整理成一篇隨筆專論,標題也做了修改,內容也隨著不斷試驗做了補充和調整。筆者認為,發現野生高粱并不重要,而發現它的軸延體才是***重要的。可以說,筆者正是通過兩年多的試驗研究,才真正體會到后稷教民稼穡的偉大歷史功績。
筆者自發現野生高粱以來,對其進行了連續地考察試驗,覺得這種從未見過的野生植物有些生態特征與其它禾本科植物差別很大,其原因撲朔迷離。當然,一個外行對于一種陌生植物的認識,需要有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因此,我采用“土辦法”,從2019年的6月至2020的3月先后搞了夏、冬、春三次發芽試驗。后來又搞了多次。至少對于我個人來說,有突破性的發現。這些試驗原來有一篇綜合實驗報告,因為電腦故障,有些資料和數據丟失。現在保存比較完整的是《對野生高粱“易地生根”現象的探索》和前不久整理的《野生高粱與三種栽培高粱軸延體對比試驗的原始數據及照片》。另外有幾篇《漫筆野生高粱的試驗鑒定》講得比較通俗。
目前在我國學術界,對于中國古代有無高粱及現代有無野生高粱存在很大的爭議,而且堅持“無”的人已經占到了“主流”地位,尤其至今尚未聽說有人發現了野生高粱;而我偶然發現了可能是我們晉南現代叫“?黍”(過去寫做“稻黍”“?”讀tǎo,晉南方言 “稻”也讀tǎo)、古代叫做“稷”的散穗高粱的野生祖本,而且很可能找到了它們之所以瀕臨滅絕的“生存密碼”;但我已經年逾八旬,而且有嚴重的腦梗。如果我突然撒手人寰,很可能沒有人繼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因此,我利用冬季有暖氣,在室溫條件下,高粱、玉米等植物基本可以正常發芽。以期在我臨終之前,能對這項研究能搞出個比較滿意的結果。
一、胚軸延伸體的發現
2019年6月11日與22日,先搞了兩次發芽,共發芽9粒,然后移植到飲水紙杯內(每杯一粒)。這里的“發芽”僅指“露白”,即剛剛露出個“白尖”就轉移到紙杯內。我的方法是把剛露白的種子放在土表,然后用細沙覆蓋。我是把它視為野草。凡是由種子繁殖的野生植物,都是“落地生根”,有誰會“種”它?如果“種”,就不可能找到它的生存規律。結果,那些苗子就像得了“軟骨病”,長著長著都倒了。隨后又在7月2日搞了“直播”試驗,即每個紙杯直接種兩粒種子,也是淺播覆沙。種了3杯,共長出6棵,起初長勢喜人,后來又都倒了。這是咋回事呀?仔細一看,哎呀!原來每個苗子的下面的一段不是莖!
這時,我在網上查到這么一段話:“大部分單子葉植物都為須根系,如高粱等。……須根系的特點是種子萌發時所發生的主根很早退化,而由莖基部長出叢生須狀的根,這些根不是來自老根,而是來自莖的基部,是后來產生的,稱為不定根……。” [1]
這段話過于簡略,這段植物體應該有個名字,以便寫材料有個稱呼。可是在網上再三查找,找不到有人給它做出定義。因此,我這個業余農科愛好者就自作聰明,暫時管它叫“胚軸延伸體”(簡稱“軸延體”或“軸延”)。
二、對“胚軸延伸體”的命名和翻譯
2020年6月份把我的試驗材料加以整理,想把它投給某期刊,需要找參考資料,先后看到幾篇文章,才發現我國高粱研究人員對它還沒有統一名稱。如:2019年9月份山西農科院品資所劉彥軍所長給我來信說:“野生高粱的典型特征是有根狀莖,等種子成熟以后可以挖開根看一下。”其實,早在他的來信之前兩個月,我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典型特征”的“根狀莖”,只是名稱不同而已。不過不用挖,它就在我的眼前明擺著。
再查“根狀莖”,其定義是:“根狀莖,亦稱根莖,地下的變態莖之一。 ……”還有許多解釋的文字,里面并沒提到高粱、玉米等的根狀莖。看來植物學上的“根狀莖”并不包括禾本科植物的這段植物體。
后來查到兩篇專門研究高粱出苗的論文,他們不僅名稱不同,而且說法有些矛盾。一篇是山西農科院庾正平等的文章[2],無論在摘要里或是關鍵詞,都用的是“胚軸伸長”,只是在公式計算和列表時,才說:“根莖長度即高粱種子胚軸伸長長度”。說明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根莖”不適宜,還得給讀者做解釋。而且在***后的“討論”中認為“高粱是上胚軸伸長”。而另一篇是吉林農科院陳冰嬬等的文章[3],在摘要中使用的是“中胚軸”,關鍵詞有兩個:“中胚軸”與“伸長特性”。由此可見這兩家的職業農科研究者都沒有個統一名稱,而且到底是“上胚軸”還是“中胚軸”伸長?說法不一,這就讓我莫衷一是。
再后來反復思考和查閱相關資料[4-5],才知道:雙子葉植物,分為“上胚軸”(epicotyl)與“下胚軸”(hypocotyl)。單子葉植物如小麥、玉米、高粱、黍子等分別是“上胚軸”“中胚軸”(mesocotyl)伸長[6-3];還有些植物如黍子是上胚軸與中胚軸都伸長[7]。我認為所有禾本科植物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名稱。于是就用了我自己的命名。
為什么我要對這個東西小題大做呢?因為我就是要把我對它的研究結果寫成文章,名不正則言不順,文章沒法寫。“胚芽”“胚根”后來都不叫這兩個名字了。“胚軸”在發芽之后,已經不是原來的形態,名字也不應該再叫“胚軸”了。因此,我仍然堅持自己的命名。如果有哪位專家覺得有錯誤,請指點迷津,本人愿聆聽教誨。
現在投稿都要求把“標題”“摘要”“關鍵詞”譯成英文。而“胚軸延伸體”如何翻譯?雖然我的子女中有人懂英語,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沒有人是學“生物”的。我這一生,命運多舛,道路曲折。40歲那年(1***)參加了太原工學院“高速水流”研究生考試,考了第二名,還參加了復試(就錄取兩名),只因英語初試成績是“18分”(一個月后的復試大概在50分左右),***后據說被一位清華學子“置換”了(聽說那位學子的英語70多分,但初試數學30多分)。隨后我通過民辦教師轉正考試,取得化學、語文“兩個單科******”。這次考試,只要有一門學科成績取得第二名,就可以轉正。隨后我的工作調到西社中學教化學。也就是在40歲才發憤學習英語,以雪“考研落榜”之恥。不過,淺嘗輒止,后來就成為我的幾個子女的英語“啟蒙老師”。因此,我對英語還多少懂點ABC。
于是我從“百度翻譯”先查“胚軸延伸體”,結果是“Hypocotyl extension ”;再用英語反查漢語,卻是“下胚軸延伸”,而禾本科植物沒有“下胚軸伸長”的說法。看來,英語里“胚軸”與“下胚軸”是同一個單詞,而且沒有復合詞“胚軸延伸體”。
當時我的外孫女丹丹是暨南大學的在校生,“雅思”考試拿到8分,已經接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優生交換公費留學的通知,在家正等待出國。于是我讓她翻譯。誰知她的翻譯跟我的完全相同。問她怎么翻譯的,她指了指電腦。又問她:“你的詞典呢?”“沒有。”原來現在學外語連詞典都不用了。于是我跟她商量,把“上胚軸”“中胚軸”和“下胚軸”共有的詞根“copyl”后面加個“extension”組成一個新英語詞組是否可以?英語的構詞方法與漢語不同,在英語中“copyl”不是一個獨立的單詞,“子葉”也有這個詞根。就這樣,我和她共同“杜撰”了這個英語復合詞。不過,這篇文稿不打算投稿,仍按正式稿件寫,在出書后給中國人看,以免被“外人”見笑。不過,恐怕英語里根本沒有這個詞組,要是有,早被別人譯成漢語啦。
三、“軸延體”在須根植物出苗時的作用
我認為軸延體在須根植物的出苗過程中有三個作用:1.有上傳下導的傳輸作用:具體說又分為:①把胚乳中的營養直接輸送給幼苗;②把初生根從土壤中攝取的營養傳輸給幼苗;③把幼苗的葉子在光合作用下產生的有機物質向下傳輸給初生根,供其生長發育。2.在出苗期是幼苗的載體和“助推器”,是它承載著幼苗并將其推出地面。不過,這是***初的認識,后來在試驗過程中,發現它把幼苗推出地面還能繼續向前推移,是平伸。3.是初生根與幼苗莖的連接段。也就是它把下面的根(初生根)與上面的莖連接在一起。當幼苗在莖基部長出不定根,形成******根系后,其歷史使命便告完成,此后便逐漸消亡。因此,軸延體是須根植物在幼苗生長過程中的一個暫時的“零部件”。它是初生根(老根)與******根(新根)之間過渡的橋梁、是接力賽的“交接棒”。不過,這一交接過程相當緩慢,在室內搞試驗,至少得40-50天才能完成。
它與雙子葉植物的軸延體不同,雙子葉植物長大成苗后,它就與根和莖融為一體,很難分清它們之間的界限;而單子葉植物是由軸延體幫助新根與莖連接在一起,當新根能獨立完成“根”的作用后,它和老根便脫離植物體,逐漸腐爛消失。
四、軸延體是野生高粱的“遺傳密碼”
當我發現了野生高粱后,就覺得野生高粱與***尾草雖有些共性,但個性更大,***突出、***不可思議的就是它的苗子大小過于懸殊。在我發現的100余棵苗子中,高于120cm的大苗只有4棵,中苗也不過20棵左右,其余都是小于50cm的小苗(袖珍苗),甚至許多小于20cm者,被我戲稱為“微粱”。我覺得它的大小苗不是由遺傳造成的,或者說它們本身就具有同樣的種子可以長出大小不同的苗子的“遺傳性”。因此,我之所以要自己獨立地搞試驗,主要尋是尋找大小苗懸殊的原因。
果然,一開始“種”它,就出乎意料地發現了這個“胚軸延伸體”。于是我就做了這樣的推理:假如有的種子恰巧落到一個深約3cm的小坑里,而且被土埋住,那就相當于有人把它“種”在那里,它就能夠正常地生長;但這種機會太偶然、太少了,絕大多數的種子沒有這樣的機會。它們如果落在平地上,也發了芽,那就只好躺下來,讓其軸延體平伸,一旦莖基部落地,長出不定根,繼而成為新根,這就叫做“易地生根”。可想而知,更多種子連莖基落地的機會都沒有,或者遲遲不能落地。落地早的,苗子長得比較好,反之,只能長出小苗,更多的是沒有出苗的機會。這樣,就形成小苗遠多于大苗的現象。
然而,這個推理雖然有些道理,但坦白地說,三年來,我沒有在公園內找到一棵這樣的小苗子。但是我搞得易地生根的試驗卻非常成功。這次試驗的時間是:2020.7.21.—9.10.歷時51天(在《漫筆之二》寫成41天,是筆誤)。這次試驗對我來說,就是“活到老學到老”,使我增加了知識:我覺得是一種樂趣,是一種享受,收獲滿滿,受益匪淺,樂在其中!
我很想把自己的收獲告訴廣大讀者,愿與大家共同分享這一樂趣。現在把幾張照片制作成拼圖(圖1與圖2):請看圖2左邊的苗子,“出苗地”與“生根地”之間大概相距幾個厘米。兩點之間的“連線”就是軸延體。拍照的時間是“8.28.”也就是播種后39天。圖右是


另一棵苗,我用白紙做背景,它的軸延體已經完全變成“黑色”的像“彎***”似的“鋼絲”,時間是“9.4.”也就是距離試驗結束還有6天。這兩棵苗都能正常生長。
圖2是******一棵苗子。莖基未能落地,但不定根已經插進土里,形成“懸空寺”。上面的大圈內是苗土分離后的照片(請注意:那棵苗子上有一條藍線,是苗土分離后用來辨認的記號),“老根”已經接近死亡;新根正在形成中。沒有記住它的編號,像這樣的情況只能長出小苗。另外“小黑”的3棵留苗中,只有一棵正常,苗高28.8cm;另外兩棵因為不定根未能入土,苗高******,只有(18.8和15cm),今后將會死去。
另外,我在2019年8月9日,把6月11日、22日和7月1日淺播的幾個紙杯中的4個移栽到公園里,26天后觀察,全部長成了“微粱”,其中有一棵還長出個小穗子,只結了7-8粒種子。后來被園藝工人割草割掉了。家里剩下的幾個杯子,再用半截紙杯加高,把土埋住莖基部,繼續觀察。結果始終都是“幼苗”,就像麥苗一樣,不僅沒有開花結果,連拔節也沒有。直到10月1日,全部扔掉了。它們就是靠初生根一直活了3-4個月!
寫到這里,我不由感嘆野生高粱好像也有“靈性”!它的老根與新根好比一個孩子的“生母”與“繼母”。這位生母已經氣息奄奄,垂垂老矣,本該就要咽氣了,就想給孩子找一位繼母來“托孤”;只因一時找不到,她還要殫精竭慮地等待著,不甘心咽下***后一口氣。她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啊!其實,這也是野生植物的生存本能,是一種自然現象。
根據我的試驗,野生高粱的軸延體要比晉中的密穗高粱的軸延體長約一倍。而且它的軸延體越長,苗子長得越高;越是裸露在************之下,越長得好(這一點與某些專業人員的試驗可能相反)。這才是它至今已經瀕臨滅絕的***主要的原因。因此,軸延體決定著野生高粱的命運,說是它的“命根子”“生命線”“生存密碼”,應該是恰當的。
2018年5月份,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能在70天后發現野生高粱。我在《再論高粱……爭議之我見》一文里,把我國“古代野生高粱”作為“假想敵”,讓***尾草與它來一場PK,結果可想而知,野生高粱完全落敗。那時候我就是比較二者的分蘗力、分枝力、再生力、結籽率……,無論哪一條,野高粱都沒法比。我僅以籽粒大小來比較:假定野高粱的種子比***尾草的重10倍(其實遠不止10倍),就靠風力傳播。又假定風能把野高粱種子吹到10米遠,***尾草的種子就在100米之外。而傳播的面積則是“平方”關系,就是野高粱的10000倍!然后根據進化論的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尾草到現在是鋪天蓋地,泛濫成災;而野生高粱已經瀕臨絕境。它“稀有”到我八十歲之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棵。
當然這只是推理。現在看來,野生高粱瀕臨絕境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的軸延體太長和換根的時間太長!聯想我在1970-74年搞得《玉米拔苗移栽,五年推向全公社》,從播種到移栽不超過20天;而高粱和野高粱若是在20天內移栽,不僅不能增產,恐怕成活都很困難。
就是在那篇《再論》里我推測:“我國北方雖然沒有人發現什么野草跟高粱有相似關系,但說不定在某些地處偏僻、人跡罕至、尤其專家們的足跡未到的地方,或許就有野生高粱。即使找不到也無所謂,既然在我國已經考古發現了大量高粱遺存,理所當然古代肯定有野生高粱。”
五、不搞野生高粱研究,就不能理解后稷教民稼穡的歷史功績!
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視察山西時說過“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要真正貫徹執行習主席的指示,不能靠幾句空話,擺空架子。首先要弄清楚“稷”是什么?后稷的主要歷史功績是什么?現在我國學術界認為稷是粟者已成“主流”,對我國考古學家發現的高粱遺存說三道四,一概給予漠視和否定。我們稷山縣也有人認為(或曾經認為)是后稷把***尾草培育成中國******谷——“粟”。我的觀點恰恰相反:如果說稷是高粱,后稷就是一條龍;如果認為稷是粟,后稷就是一條蟲。為什么?
根據我國考古發現,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北磁山就有人工馴化的粟,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也有粟的發現。為什么后稷不是出在河北磁山和西安,卻是在山西的稷山呢?為什么我國南方考古發現了大量稻的遺存,北方也有大量粟的遺存發現,高粱遺存卻少得多,而且多有非議?為什么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姬棄能被歷史尊為后稷、稷王、五谷神?其實道理很簡單,人常說“物以稀為貴”;如果大熊貓多到遍地都是,它就不是“國寶”了!
為了論證我的觀點,先討論我國考古發現的真正高粱究竟在那里?
1.鄭州大河村的糧食遺存究竟是大豆還是高粱?
我是在網上看了劉夙的《高粱:來自非洲的毒品……》,才知道鄭州大河村的糧食遺存被美國人拿顯微鏡“考”出個“大豆”來,才決定參與這場爭論的。
那時候我對高粱的知識,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但可以肯定中國古代有高粱。主要原因是我16歲去山東濰縣讀書一年,知道濰坊地區的人把我們稷山的“?黍”中硬粒的叫做“稷子”,軟的叫做“黍稷”。那里廣泛種植的是比較高產的“秫秫”。因此,我覺得山東在歷史上曾經種植的是“稷子”;假如我國有外來品種,只能是后來引進了外國的高產品種。
當時我說我只會“考今”,不會考古。就拿了一粒普通大豆,用簡單的計算方法,即體積比=平均粒徑的立方比:v/V=d3/D3,求出根據劉夙提供的照片上各種顆粒體積的比是:大河顆粒:現代野大豆:現代高粱:現代大豆=1:1.57:2.90:18.34。
于是我說:“請看:五千年前的大河村人,辛辛苦苦地把野生大豆‘馴化’了也許幾百年,結果其籽粒還不到現代野生大豆的三分之二;一顆現代高粱幾乎是它的三倍;現代大豆更是它的18倍!這還叫“馴化”?完全是野草!那幾位美國人硬說它是‘大豆’,實在令我難以置信!”
接著就是那幾句“豪語”:“人常說‘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我并不排外,如果他們念的是‘真經’,說的是真理,我唯真是從,唯理是聽;但絕不會唯名是從,唯洋是聽。我尊重專家,但不迷信任何專家。”
老實說,當時我說它“完全是野草!”,只是一句氣話。想不到幾十天后居然在一個地級市的公園里發現了野生高粱。這簡直是又一次“天助我也”!
2018年的8月1日我發現了2號野高粱,立即聯想到大河村的所謂“高粱”,極有可能就是野生高粱(古代叫“稗”)的種子。3日,幾個兒女要給他們的母親過“八旬小壽”,我與女兒安梅一家人都到太原。我就把一個小穗拿到太原,讓我的孫女用手機拍了兩張照片,一張畫著比例尺,已經公開過。現在我把第二張跟劉夙的照片做成拼圖加以對照,請讀者看看我的推斷是否合理(圖3)。
現在我基本可以斷定:這是五千年前大河村人采集的古代名叫“稗”的種子,或者是正在馴化中的高粱種子!我這個“考今”的把式,極有可能解決了這個考古難題!而且凡是與大河村遺存相似的疑似“高粱”的糧食遺存,只要其顆粒小于高粱,大于黍子,都可能是稗的種子。中科院李璠的結論應該予以肯定,它雖然不能算是真正的“高粱”,但應該是“準高粱——稗!”據說我國當代***權威的考古學家安志敏對大河村的考古發現持有異議。這可以理解,因為它的籽粒確實太小;安志敏拿到北京植物園讓那里的專家鑒定,但他們只是說不是高粱,卻沒有說出是什么。如果安教授泉下有靈,他看到這張照片也許會心服口服。
2.中國古代有沒有高粱?它的源頭在哪里?
有!就在稷王山下的萬榮荊村。這是本地區考古學家衛斯先生的結論。為什么衛先生不說是在鄭州?大河村的“高粱”距今5000多年,有點太早;萬榮荊村就是后稷教民稼穡的地方!我***近查到,衛斯把他的文章做了補充改寫,標題是《中國高粱從哪里起源?這里……》。這里考古發現的高粱遺存距今大約4000多年,基本就是堯舜后稷生活的時代。這篇文章里還收錄了我發現的3張野生高粱照片。

為什么我說稷如果是高粱,后稷就是一條龍;如果是粟,后稷就是一條蟲呢?
①先比較高粱與粟的野生祖本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間。現在一般人都說粟的野生祖本是***尾草。而***尾草的生存空間要比野生高粱(稗)之大,絕不止一萬倍,恐怕數以“億”計,都差得很遠。尤其是我發現了“稗”的軸延體特別長,它的生存就更是難上加難。
既然野生高粱要比***尾草的存在難之又難,可想而知,我國古代先民***早、***容易馴化的是谷子而不是高粱。現在查到衛斯的兩篇文章[8-9],我國古代采集或馴化***尾草的起始年代和地點是:2.4萬-1.6萬年前的晉東南沁水下川遺址,處于舊石器時代的晚期。雖沒有發現糧食顆粒遺存,但發現有用以糧食加工的石磨盤。***早發現粟的遺存是河北武安磁山。前面說距今7000年,現在據說用碳14測定是8000年。全國考古發現的史前粟的遺址就有44處[8]。
而至今發現的高粱遺存只有13處,其中也只有大河村距今5000年,萬榮荊村距今4000多年,甘肅民樂3400-3700年。這3處可以算是“史前”,其余都是西周、漢、唐時代的墓葬等遺存[9]。看來,高粱(包括疑似)的考古發現與粟比較,只能算“鳳毛麟角”而已。但是,就算再少,就算是“稗”,總不能說是外來的吧?因為,按“外來說”***早應該在元代。可見,如果稷是粟,后稷是“龍”,是否“龍”就太多了?神州遍地皆“后稷”!
②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容易,做起來就不知道有多么難。依我看在五谷中,***難“樹”的不是粟,而是高粱。為什么?就是因為它有那么一段被我稱之為“軸延體”(別人稱為“根莖”“中胚軸”)!我******次“樹”它們,就沒有“樹”起來,還鬧了個笑話:我在每棵苗子旁邊插個柴棒,用塑料繩拴起來,強迫人家“樹”,結果害得它們3-4個月還是“幼苗”!再后來采用“淺、中、深”三種“樹”法,***后采用4cm,終于“樹”成功了。
我自2019年6月至2021年5月,歷時兩年,搞了10次以上的試驗,可以說,“濃縮”了古代勞動人民對高粱從采集到農耕的歷史過程。我現在才仔細看了庾正平等的文章[2],據說我省中、北部農民種雜交高粱,有一句諺語:“一寸全苗。二寸缺苗,三寸無苗”。他們就是尋找培育“根莖”長度在8-10cm的雜交高粱品種的父母本組合的。可見,***難“樹”的農作物是高粱,而不是谷子。為什么谷子、小麥和綠豆用耬種,玉米、高粱、棉花要用犁種?這是幾千年先民的歷史經驗。
正是我國黃河流域的古代先民,也許經過上千年的摸索,把一種瀕臨絕跡,生存能力很差,生存條件苛刻,產量很低的“小草”,經過不斷馴化、人工選擇,把它培育成一種植株高大、產量******、既耐旱又耐澇,可以廣泛種植的糧食作物,不知拯救了多少代黃河人。而這些古人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原名叫姬棄、被周部落尊為始祖、被后人尊為稷王、五谷神的后稷!我稱他為古代的袁隆平,應該不是夸張。
現在有些高粱研究專家說稷是粟 ,恐怕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我國考古發現的粟***多、***早;而高粱不但少,而且多有疑義。這些專家們的思維方法是否可以換個角度啊?
本文中提到的“稗”究竟是啥東西?請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我國古籍里早有野生高粱記載——兼﹤爾雅翼﹥中的“稷”與“粱”》。
參考文獻:
[1]這幾句話是 在搜***百科上查得,作者、書名不詳.
[2] 庾正平,任建華.高粱出苗能力的遺傳研究[J]華北農學報1986年第1卷44頁.
[3] 陳冰嬬,李繼洪,李淑杰等.不同類型高粱中胚軸伸長特性的研究[J]作物雜志2016年03期1-5頁.
[4]葉創興,朱念德,廖文波.植物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盧慶善.高粱學[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
[6]鄭相如,范雅蘭.胚軸——有胚植物的一種特殊結構[J]生物學通報1998年第33卷第5期10-11頁.
[7]周德超.再談禾谷類種子萌發過程中胚軸的伸長[J]生物學通報1991年09期10-11頁.
[8]衛斯.試論中國粟的起源、馴化與傳播[J]中國農業1994年2期
[9]衛斯.試探我國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論萬榮荊村遺址出土的有關標本[J]中國農史,1984(2)第45-50頁.
2021年1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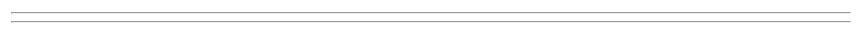
監制/梁斌 主編:李順利 、賀曉云
編輯:吳元庚、程 衛
關注攜手
轉發支持
